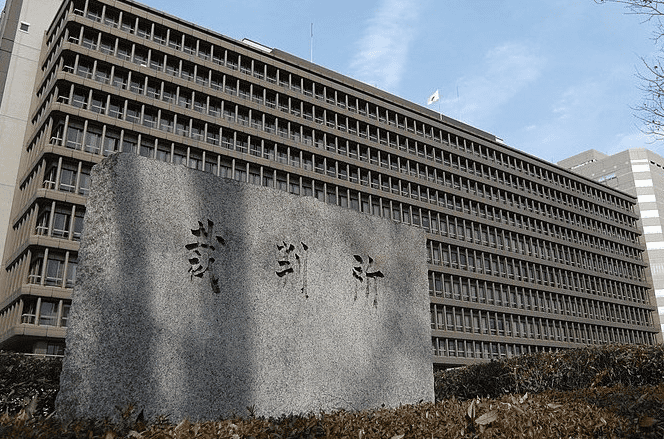日本曾在大正時期採取陪審制,1943年因二戰戰況嚴峻,陪審制喊停。隨著戰事終結,陪審制卻未能復甦,往後超過一甲子,日本司法都是採取職業法官的刑事審判制。
2004年由小泉純一郎所領導的內閣,在國會提出《裁判員法》(さいばんいんせいど),日本裁判員制度正式確立。5年後,2009年8月3日,東京地方法院進行了第一次的裁判員刑事審理。
被告男性因在東京足立區刺傷一名女性,遭判處15年監禁。根據朝日新聞報導,這場審理花了四天時間,從2萬7700名裁判員候補名冊中,抽籤選出了100位候選人,經過甄選確立6名裁判員,與3名職業法官一同進行審判。
日本改採裁判員制度,無非是司法的重大變革,民間是如何看待人民參與司法的新氣象?根據日本最高裁判所的統計,2018年該年度,民眾在被選任為裁判員前,僅有3成9的人對參與審判感興趣,其中更只有1成2的人有高度熱忱。
台灣即將於2023年上路的《國民法官法》便是移植自日本裁判員制度。許多人質疑,讓未受法律專業訓練的平民直接參與定罪、量刑,除了擔憂人民受到法官不當影響,也有輿論指出,參審制是否只是將全民公審的風氣搬上法庭?
迎接令和元年的同時,日本最高裁判所也公布「裁判員制度10年的總結報告書」,以量刑、審理時間等具體數據,展示了自2009至2018年間,十年來司法制度變革的影響。P#新聞實驗室透過七張圖表,解析日本推行裁判員制度後,量刑與案件審理發生了什麼變化。
性犯罪案件量刑偏重 保護觀察處分增加
日本裁判員制度的適用案件範圍以足以判處死刑、無期徒刑的案件,或是必須通過合議庭審判的重大刑案為主,包括殺人罪(含既遂與未遂)、傷害致死罪、強姦致死罪、建物縱火罪等。
從2009年新制上路以來,裁判員審判的案件占比一直不高,約落在1.5%至2.1%之間。以2018年日本當年度6萬9028件刑事一審案件為例,符合裁判員審判的刑案僅有1090件,佔該年度1.6%。
雖然案件量不多,但在量刑方面,特定的刑案類別,與過往職業法官判決結果相比,出現明顯差異。
在傷害致死罪的刑案中,職業法官審判時期,有六成的量刑皆落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;但裁判員審判推行後,六成的案件,量刑提高分布在五年至九年的有期徒刑,有偏重的趨勢。
量刑偏重的變化,也可以在性犯罪相關的刑案中發生,在強制性交與強姦致死罪案件中,職業法官審判時期,半數案件落在5年以下至7年以下有期徒刑;但來到裁判員制度時,七成的案件分布在7年以下至15年以下有期徒刑,量刑更加多元。
然而,在殺人既遂的案件卻展現不同趨勢。裁判員在殺人既遂罪量刑時,三年以下緩刑的比率提高——儘管量刑高點落在11年以下至19年以下有期徒刑,但整體而言,量刑較職業法官時期輕。
同樣地,在建物縱火罪中,三年以下緩刑從職業法官制的25%躍升至40%,五年以下徒刑則降低了一成,為統計中變化最大的罪刑。
同時,裁判員制度也更加重視犯罪者的教化。日本的保護觀察制度,是隱含教化、輔導的罪犯處理方式。內容包括暫緩執行刑罰,並受相關組織觀察、約束,防止再犯。裁判員制度上路後,裁定保護觀察的比例從過去的3成5,上升至5成5。可以見得,大眾加入刑事審理後,更願意對犯罪者提供嚴刑峻罰之外的更生協助,展現國民情感融入司法審理的參審制特色。
虐兒案從重量刑 最高裁判所罕見撤銷原判
裁判員的量刑雖反映了民情,但也非完全沒有量刑爭議,日本2013年就曾出現裁判員量刑過重,遭最高裁判所撤銷判決的案例,裁判員制度的量刑難題浮上檯面。
根據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院第689號判決,2010年1月27日深夜,一歲八個月的女童遭父母毆打,頭部被用力撞擊地面,導致急性硬膜下血腫,送醫不治。檢察官當庭求處父母雙方各10年的有期徒刑,經裁判員一審宣判,二名被告各判15年有期徒刑。
裁判員認為,父母虐待兒童致死是危險且充滿惡意的行為,因此處以重刑。被告上訴至最高裁判所,審理後撤回原判,對二名被告改求處10年及8年有期徒刑。
職業法官判決比裁判員判決為輕,主因有二:首先,最高裁判所認為,一審裁判員的審判應該符合客觀、合理等原則。但一審判決中,裁判員以虐兒事件為社會所不能忍的原因,要求科以嚴苛刑罰。最高裁判所認為,裁判員以「社會風氣」為由大幅提升量刑,超過檢察官所求處的刑度,且不符合量刑檢索系統的量刑範圍。判決並不合理,也不具說服力,因此撤銷原判。
其次,最高裁判所法官也指出,擔任裁判官的職業法官應充分說明案件中的重要事實,讓裁判員能充分理解,但本案的裁判官並未善盡職責。
日本裁判員制,二、三審皆是由職業法官審理,為尊重裁判員的判決,除非一審中有程序瑕疵或是裁判員明顯失職,否則皆會尊重一審原判決。因此第689號案件的改判,實為罕見。參審制的優點在於將「民情」融入審理,提高司法民主化程度,但此一案也反映裁判員可能過度投入情緒的風險。
審理時間逐年升高 裁判員辭退率亦攀升
除了量刑變化,案件審理的時間也出現改變。2009年、裁判員審理制度上路第一年,平均開庭時間為526.9分鐘,終局評議時間為397分鐘。但制度實施十年後,終局評議時間近乎翻倍,耗費778.3分鐘。
司法院發言人張永宏根據考察經驗解釋,開庭時間變化不大,評議時間逐年升高,代表「評議」在審理過程中越來越重要。「評議的時候不充分,後面就是一個草率的判決,它一定是連動的。」評議時間拉長,反映出裁判員與職業法官花費更多時間做逐一爭點的討論,張永宏認為,審理時間變長,是裁判制度可預期的變化。
雖然案件性質、內容有差異,但裁判員審理耗時更長,是不爭的事實。若以歷年平均審理案件所需的總日數來看,數字直線上升,2009年僅需花費3.4日,但2018年卻得花上6.4日,對兼職的素人裁判員而言,稱得上是負擔。
2015年,被稱作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「最後逃犯」的高橋克也在東京落網。1995年,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發動沙林毒氣襲擊,造成13人死亡、數千人受傷。共犯高橋克也逃亡17年後遭逮,成為奧姆真理教恐怖分子中,唯一適用新法,以裁判員制度審理的罪犯。
全日本新聞網報導,為了這次的審判,東京地方裁判所破天荒從裁判員名冊中挑選了650名候選人,多數人相繼辭退,最終從86人中選出6名裁判員。
根據日本媒體報導,這次的審判也創下39次公判開庭的紀錄,該案裁判員的在職日共計113日,最終判處高橋克也無期徒刑。
參與審判的裁判員有家庭主婦、一般上班族,他們紛紛表示:「離開公司很長的時間,造成公司困擾」、「我是家庭主婦,要帶小孩,所以有相當程度的困難。」當遭遇重大刑案,裁判員往往得耗費超出預期的時間,參與審理。
翻開日本最高裁判所統計,裁判員制度實施的第一年,裁判員辭退率為53.1%,到了2018年,上升至67%。張永宏解釋,日本曾對裁判員高辭退率進行分析,除了審理時間變長之外,經濟不景氣與少子化都是原因。
雖然難以詳細分析每一位裁判員的辭退理由,裁判員是制度核心,近七成的辭退率是否能維持裁判員制度運作?為參審制度埋下隱憂。
台灣國民法官法,師法日本裁判員制度。日本這份「裁判員制度10年總結報告書」在在量刑與審理時間上,提供借鏡。讓未受專業訓練的平民參與審判,在合法、合理之外亦合乎民情所盼,固然能推動司法民主化更進一步,然而素人法官在刑期定罪判斷爭議,審理過程曠日廢時,以及是否也會有高辭退率現象,都是台灣正式實施國民法官制時,必須審慎思考的問題。在司法民主化、杜絕恐龍法官之虞,如何避免國民法官過度感情用事,以及妥善處理重大刑案審理的時間成本,值得深思。